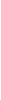恶人还需恶人磨
大雨如瀑,挟带丝丝寒意。
雨水落在人工湖上,泛起圈圈涟漪。
洛熙晨心不在焉的在凉亭焚香听曲。
她知道自打二人确认关系后,君陌璃对她的占有欲向来极其强烈,但那日那样粗暴的强取豪夺、占领她身体的君陌璃,她还是第一次见,看来阎凌是真的让君陌璃感受到了威胁。
回想起那日君陌璃在房中那狂野而任性妄为、横行霸道的模样,洛熙晨面颊不自觉又泛起一层红晕。
蓦然间,她察觉周身异动,霎时从回忆中回过神来。
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她的视线范围内。
北冥从长廊的尽头由远而近来到她身旁,弯下腰在她耳边耳语。
洛熙晨的目光猝然一变,微微瞇起双眼:「集结人马,入夜就出发。」
这次的目标是岚州刺史---韩元章。
深夜,马蹄鞑鞑,雷电交加。
洛熙晨刚出城不久,阎凌这边也迅速收到灵泽的消息:「主人,洛熙晨连夜带了一队人马冒雨出城去了,看方向应该是要去岚州。」
事出反常必有妖。
洛熙晨在京城待得好好的,没事跑去岚州做什么?
更何况她还带着一票剑雨楼的杀手。
閰凌心中一沉,暗道不好:「赶紧备马!」
岚州刺使韩元章本为穷乡僻壤的一名穷书生,家徒四壁,一贫如洗。
当年韩元章赴京赶考,却不慎名落孙山,后来在机缘巧合之下认识了独孤德康的独女—独孤兰鸢。
独孤氏一族为世家大族,皇亲国戚,门第显赫,于政、于商都有着不可轻易撼动的地位,于是韩元章便想方设法去接近独孤兰鸢,倾尽所能、用尽各种花言巧语去讨得她的欢心。
独孤兰鸢毕竟为大家闺秀,不谙世事,加之当年的韩元章也称的上是玉树临风、仪表堂堂,几次三番下来,独孤兰鸢便被韩元章给拿捏得死死的,非他不嫁,甚至不惜假孕,自毁名誉,以死相逼,威胁父母。
见自家宝贝女儿心意已决,又唯恐自家女儿为爱做出更加激进的傻事,独孤德康不得已只能妥协。
韩元章就这样一夕翻身,成了独孤家的上门女婿,仕途从此平步青云,一帆风顺。
起初二人相敬如宾,举案齐眉,曾一度为众人所称羡,然而这样琴瑟和鸣的日子并不长久。
随着韩元章的官位越来越大,韩元章的真面目也逐渐露出马脚,暴露无遗。
在外他是个为人称道、礼数周全的谦谦君子,然而私底下的他对待发妻却经常是暴力相向,每每喝醉便拿独孤兰鸢出气,恶行恶状罄竹难书,数不胜数。
独孤兰鸢为了自己的一双儿女,不忍儿女在支离破碎的家庭中长大,便选择再三隐忍、任打任骂。
她也不敢向娘家诉苦,毕竟当年她的父母早已看出韩元章接近自己的女儿是别有居心,自然是极力反对这门婚事,是她自己被爱情冲昏了头,失了理智,坚持非嫁给韩元章不可。
奈何她十五年来的委屈求全并未因此换来丈夫的回心转意,反而使韩元章变本加厉。
夜深人静,万籁俱寂。
一道女人凄厉的尖叫声响彻天际。
韩元章近来新得到了一件世所罕见、人人争抢的宝贝,自是欣喜若狂,毫无悬念又是喝得酩酊大醉。
他一喝醉,倒霉的自然是独孤兰鸢。
独孤兰鸢出身名门,而今又是高官之妻,本应是日日穿金戴银,珠翠满头,打扮得雍容华贵,可现下她却像个路边乞丐般落魄不堪,披头散发,嘴角还挂着血丝,周身上下遍体鳞伤,旧伤未愈又添新伤。
韩元章手执皮鞭,不断的抽向独孤兰鸢,下手之狠,毫不留情,就像是在抽打牲畜一般,哪怕独孤兰鸢浑身发抖着向他跪地求饶,他也毫无动摇,没有半分要停手的意思。
韩元章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,以至于根本未曾察觉府内动静,连自己府中上下已被剑雨楼杀了个精光也未曾发现。
就在韩元章手中的鞭子准备再次落下之际,一名小厮一瘸一拐、上气不接下气,急冲冲的向他跑来。
「主人,不好了……剑、剑雨楼……」
那小厮话未说完,便被一剑穿心,当场倒地。
洛熙晨惬意缓步上前,周身威压逼人,看得韩元章止不住瑟瑟发抖。
果然恶人还需恶人磨。
洛熙晨像是根本没看见韩元章似的,径直走向此刻犹如惊弓之鸟,跪坐在地的独孤兰鸢,伸手轻轻抬起她的下巴,只见那张本该标致的脸蛋上满是伤痕和泪痕。
洛熙晨在独孤兰鸢身前蹲了下来,将脸凑到她耳边,细声蛊惑。
「当年他一无所有,是你助他咸鱼翻身,他能够飞黄腾达也是仰仗你母家鼎力相助,如今他便是这样报答你的? 听闻去年你怀孕期间他对你动辄打骂,丝毫不顾及你身怀六甲,以致你不幸小产,而他却仍旧对你毫无怜悯之心。我还听闻当年你即将临盆之际,他上青楼寻欢作乐,对你母子二人不管不顾,甚至还想休了你,迎娶那青楼女子为妻。你堂堂皇亲贵冑、名门千金,如今却沦落至此,我都替你感到不值。」
一道闪电划过天际,伴随着一声轰隆雷鸣。
独孤兰鸢双手摀住耳朵,不断摇着头,浑身剧烈颤抖着,往事一幕幕在她脑海中飞速重演。
这些年她是怎么熬过来的,恐怕连她自己都不知道。